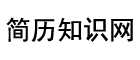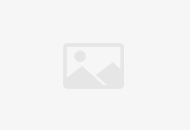【编者按】在历史学和历史书写的世界里,有学院派出身的研究者组成的“庙堂”,也有非科班出身的通俗历史写作者构成的“江湖”。前者仿佛是泉源,是知识的起点和源头,在艰深的领域里耕耘,设定历史学的框架和疆域;后者则是河流,将前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众科普,百川奔流入海,真理方能深入人心。没有“江湖”的“庙堂”最终必然失去现实关怀而只能退守象牙塔,甚至沦为人们批判的“资产阶级趣味”和“Arm-chair Scholar”;而没有“庙堂”的“江湖”则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沦为“民科”,令人贻笑大方。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知识圈,应该是上述两者的有机统一。
“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”栏目一直注重勾连学界和大众,在两者间搭建一座知识的桥梁。我们注重学界的前沿动态,关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最新进展。我们也同样重视通俗历史书写与科普等“讲故事的人”。在小说和当代史学兴起之前,人类社会有着大量的说书人群体,从本雅明到莫言,都对“讲故事的人”有过生动的描绘,这个群体承载了民间的记忆,传承并演绎了一个个民族的史诗和神话。“讲故事的人”这一群体在当下的中国也同样重要,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,讲的人和听的人可以不用在同一个空间,讲故事的形式也愈发多样。在这个系列里,记者对一批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写作和科普者进行了采访。本文为第一篇。
对于豆瓣用户和文史爱好者来说,“维舟”这个名字一定都不陌生。“维舟”真名沈茂华,1977年生,上海崇明岛人。从2004年7月起他开始写博客,那时博客的名字还叫“维舟试望故国”。被问到为什么取这个名字,他说当时注册的时候原本想取的名字都被别人先注册过了,一气之下就截取了当时很喜欢的姜夔词里的一句“维舟试望故国”,才注册成功。当时他还在厦门读大学,回望故乡远在天北,这句诗让他感慨良多。但这个名字有些太长了,后来别人渐渐就习惯只用“维舟”二字来称呼,而他也默认了这一称呼。
维舟
维舟本科学的是新闻,写作起来却涉猎驳杂,以文史为主,旁及社会学、人类学等。他在诸多媒体上都有自己的专栏,写书评也写杂文,甚至还写小说。文章的主题包罗万象,古今中外,从吃喝拉撒到信仰与宗教,都在他的观察范围内。若是你乍一听说,看到这么大开大合无所不及的文风,可能会觉得维舟是一个“民科”。可是刘擎却说,读维舟的书评,是了解一本书最省力的路径。“民科”往往不在意学术共同体的评价,但维舟的考证文章却让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历史教科书做出了修正。
米歇尔·福柯在他的名著《知识考古学》当中提出了“知识考古学”的研究方法,即用类似考古学研究地层学的方法,重新理解和考证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是如何产生的。在维舟的文章中,“知识考古学”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。他的文章直指我们约定俗成的传统,世代沿袭的观念,去考证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诸多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而成的。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人何以能够对历史问题有如此深入的研究?他的问题意识又是如何萌芽的?作为一个忙碌的广告业工作者,他是怎么做到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年读200本以上的书并且笔耕不辍的?带着这许多的问题,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专访了维舟先生。
澎湃新闻:我知道您原来学的专业并不是历史。您最初是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?能否请您谈谈您最欣赏、钦佩的历史学者和著作?
维舟:我对历史的兴趣很早,从小打基础的就是中国古典文史,也因此深受“文史不分家”、“以史为鉴”的传统影响,这促使我尽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,同时也有了一种试图探究某些历史问题根源的冲动。
和很多男孩子一样,我小时候也爱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和《说岳全传》,这种讲史类的演义,可说是中国的特殊传统。这些通俗历史常常带有浓厚的正统观和道德色彩(特别是“忠奸”之辨),但对孩子而言,就很容易被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带入到历史情境中去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,才会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究历史真相的求知冲动。
例如,那时历史教科书上提到历代都面对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这一波波的北族,他们按人数比汉族少太多了,但为何总是层出不穷,除了建造长城外似乎拿他们没办法,这就此成了我一个长期想了解的问题。我后来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受问题所驱使的,因而有时看起来东鳞西爪,不成体系,但对我本人而言,那都是我有强烈冲动想解决的问题,因此每次梳理清楚,也会让我涌起一种愉悦感。
我欣赏、钦佩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著作也因此多是这一路的。除了像司马迁《史记》这样气象宏大的公认巨著之外,我偏好那种运用多领域思想资源、语文学等多种工具,阐幽发微从现有文本中解读出新知新解的学者及其著作。在这方面,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、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所体现的“文史互证”及其诸多著作中运用胡语、新思想解读古史,都可说是典范,顾颉刚从民俗学出发考察古史也是开创之举。在国外学界,像海登·怀特结合文学修辞来解读历史文本的《元史学》,对我启发也很大,爱德华·萨义德的《东方学》通常被视为文化批评,但其实内在理路是接近的。在这方面,我特别反对历史学自设限制,它不妨坦率承认在理论上不能自足,可以、也必须开放,大胆借入不同学科的理论思想,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,因为“历史”本身与其说是一门“专门”的学问,不如说是关于人类处境的综合、普遍的认知。
澎湃新闻: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阅读和写作的历程?是怎么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?最初在Blogbus,后来在豆瓣,您是有意识地去跟读者互动,建立受众群的嘛?
维舟:我开始系统地读历史著作是从高中时期起,那时一心想将来研究文史,因而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全是各校中文系或历史系,但结果却因高分落榜,误打误撞被调配去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,读广告学专业。起初这让我相当苦闷,同学也不理解我的爱好,去学校古籍室查阅县志,里面的工作人员诧异说:“我在这儿十年了,第一次遇到新闻系的人来查阅线装书,还是本科生。”
当时新闻系必须辅修社会学、心理学和传播学,这些科目我原先既不了解,兴趣也不大,看起来和历史也无关,但它们却给了我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。读的历史多了,我也渐渐意识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单靠历史学本身无法解释,需要与社会学结合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“社会学之父”孔德的出发点之一也正是如此。社会学与人类学又密切相关,于是我又顺藤摸瓜开始啃一些人类学,以及后来与历史问题相关的神话学、民俗学、历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著作。我在大学里的专业、后来的工作均与历史学无关,术业无专攻,反倒也没有包袱,就随着自己的兴趣,一路跌跌撞撞,触类旁通,逐渐一点点搭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。
当然,这样读书也有很大的问题,一是不够系统,二是缺乏专业训练,三是难以与学界交流,自我摸索中,甚至也不清楚自己走的路对不对。不过,网络的兴起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,接触文献、新知都空前简便,互动、反馈不必说更及时得多了。毕业后有五年,我一直忙于工作,但2004年7月开始在blogbus写博客之后,渐渐地居然开始得到了一些认可。2012年后主要转向豆瓣,也是因为那里的氛围更好,得到的回应更为专业。
所以,应该说,不是我有意识地去“建立受众群”,我原本只是写自己感兴趣的问题,但网上的互动不但给我信心,也在不断修正我的知识体系。2009年有一次,我在读过刘浦江著《松漠之间》一书后写了书评,结果很意外地被刘先生的学生看到,转给了他本人,他事后居然联系到了我,和我通邮讨论一些相关问题。我原以为他对历史上“五德终始说”在南宋之后消亡的看法更多是一个结论而非可探讨的问题,但承他见告,才知道他关怀的视野不仅于此,而是跨出了辽金宋史的范畴,往下涉及到近代的正统论。在刘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后,他的门人邱靖嘉还找到我,说我和钟焓的书评,是刘先生生前认为对《松漠之间》的评论中写得最好,他又帮我订正、补注文献出处,收录到了纪念文集之中。这些都可说是意外的收获,也部分造就了今天的我。
澎湃新闻:看您的文章,写得很杂,关注的问题很多,却也很深。我发现您现在的文章,关注的点,很多都接近于观念史,考察一个观念、说法或信仰是如何产生,有点像福柯所说的“知识考古学”。想知道您是如何策划选题的?又是如何组织材料的?
维舟:其实我没有“策划选题”,我的很多问题,都是在阅读中自然涌现的,因为读的书就杂,所以“选题”也就显得杂。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,我觉得新知的出现不是那种“命题作文”,有了命题之后设法解决它,而是“知识的联结”——我读到某一点,突然触发了我原先对相关问题储备下来的知识,然后顺着这个点深入开挖。大概正因此,我的思路自然地就趋向于某种“知识考古学”了,因为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些文本背后隐藏的观念。毕竟历史就是人,只是有时文本本身不会说话,需要我们复原、代入那个历史语境,来体认当时人们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很多现代人费解的谜团,说到底也许就是因为后人已不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,因而按我们通常的观念总是无法破解。
前一阵刊发于“澎湃·私家历史”的那篇《中国人崇拜的龙究竟是什么?》,写作的契机就很偶然。我是在读罗新《有所不为的反叛者》时,注意到他将“忽律/骨律”一词比对为突厥语,这个结论让我深感怀疑,因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古历史上,该词可以兼指鳄鱼、勇士和乐器(琵琶)。由历史语言学入手,我推测这更有可能是“夔”的上古复辅音的分化,这可以满足三个看似相去甚远的词义,也证明在古人心中,夔龙与鳄鱼是同类。“龙”究竟是什么,向来众说纷纭,但语言学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蛛丝马迹,而人类学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何以将之神化,因为这说到底毕竟是在文化中生成的,最终,我认为这源于一种特殊的观念,即中国人对神灵“整全性”的认知不注重其纯洁性,恰恰相反,是无所不包、无所不能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我读书之杂,恰好可以帮到我从多角度切入来探究问题。
澎湃新闻:看您在豆瓣和澎湃问吧上都跟网友们有过交流和互动,谈您是如何读书的。我看您说一年要读200本书以上,很好奇您是如何做到的?又是怎么做读书笔记和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?
维舟:这个也往往只是“熟能生巧”,书读得多了,有些地方就可以快点翻过去。我大学里刚开始读人类学著作时,也是硬着头皮才啃下来的,但读得多了,熟悉了那一套学术范式和语言,渐渐地就觉得不那么难读了;更何况有很多观点,在不同的书里会被反复讨论和征引,如果有基础,就不必停下来一字一句看了——不过我还是习惯于从头到尾通读,除了某些工具书类,才在有需要时查阅相关条目。当然,除了工作、陪孩子、做家务之外,我也几乎把自己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。
维舟家中的工作室
相比起阅读,做笔记其实往往更耗时,我读完每本书都会做笔记,通常是摘抄,但涉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,会做好tag或另外记录存档,以备下次看到类似问题时,迅速勾连起来,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,问题和思路逐渐成形,有空梳理,就可以写下来了。
澎湃新闻:阅读和写作都不是您的主业,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平衡工作、生活和写作的,怎样做这个时间管理的?
维舟:这是个好问题。我的本职一度相当忙碌,早年加班加点很多,而且下班后往往还静不下心来,读不进书;但到后来,我开始强迫自己读书,学会快速“切换”状态,一旦下班,就不要多想公司的事。所以有一次“澎湃问吧”中,有人向我提问说,读书静不下心来怎么办?我的回答是:“静下心来”不应该是读书的开始,而是结果。这确实是我的经验之谈,对我而言,读书具有某种“镇定剂”的功用。
很多朋友都曾好奇地问我:“你哪来的时间?”确实,我的工作一度非常忙碌,往往就算早下班,回到家吃完饭、洗完澡也8点了,如果工作上又临时冒出什么事,同事电话进来,那这一晚就做不成什么事了。所以对我来说,如果还想读书、写稿,必须尽快切换状态。这不是等到“状态放松下来”再读书,而是不管怎样,先读起来,慢慢地沉浸进去,就放松了。久而久之,我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排除干扰,读任何自己手边的书,而且由于时间的碎片化,“断点续传”也很重要。
当然,这也需要意志力、规律性的长期习惯,以及时间管理的技巧。家里的日常生活当然也是时间管理的一环,除了家人的理解,其实对我而言,做家务有时本身就像是读书之余的休息。在这一点上,我的工作对我倒是也有帮助。广告是讲求不断创新的行业,而我所做的具体工作,又是和数字打交道,非常在意精确性。因为节奏快,总是处于多任务状态,所以必须今日事今日毕,明天要交的东西,今晚就算通宵也能做出来。这就逼得人不得不去提高效率,安排好进度,有次还和几位作家朋友开玩笑说:“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。”
书房一角
澎湃新闻:您近几年写过的最满意的文章是哪几篇?能否请您更进一步谈一谈理由并介绍下这几篇文章?
维舟: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想过。实在要说的话,我想或许可以列举这几篇:
《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》(书评,刊“见书”),这篇是评《龚鹏程述学》一书,旨在讨论现代中国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,我同意“传统可以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思想资源”,但认为复古是不可能的,最终只能是“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”,龚先生本人据说对这篇书评也颇为赞赏。
《赤壁之战的另一种可能》(刊“腾讯·大家”):本文聚焦于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博弈,讨论赤壁之战时,双方为何不能妥协,尤其是孙权何以冒险一搏,这种无法妥协的博弈,可说是中国政治的悲剧。
《黄道婆之谜》(刊“澎湃·私家历史”):黄道婆的真实史料其实寥寥无几,但却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历史话语,我认为这些衍生话语本身也值得研究,它真实地折射出了人们真正的兴趣不是了解历史,而是利用历史。
《齐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》(刊“澎湃·私家历史”):周振鹤先生曾提出,齐国也有望统一天下,那样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,但我分析认为,这是不可能的。齐国的权力结构受制于多元的封建势力,这带来开明的政治局面,但却不能在当时的局势下,将自己的经济等各方面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,从而在总动员化的残酷战争中胜出。
《“庖丁解牛”新解》(刊“澎湃·私家历史”):以往这普遍为视为一个寓言,但我试图将它“再历史化”,认为庖丁这样重技能的观念,正是在铁器工具兴起之际的思潮,而他本人之“解牛”很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。这本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家观念:庄子讲述这个故事,真正的用意恐怕未必是“养生”,而是为了倡导一种重整秩序的政治哲学。
《中国人崇拜的龙究竟是什么》(刊“澎湃·私家历史”):以往的思路都试图找到龙的“原型”,将某一种动物与“龙”进行比对,而我认为,“龙”确切地说不是“一种”动物,而是“一类”动物;因为古人的巫术思维符合所谓“相似律”,把相似的动物看作是同类。最关键的是,对农业文明的中国人来说,能陆能水(加上飞翔功能后还能上天)的“龙”出入不同界限,这种无所不能的神能才是它受崇拜的文化心理。
这几篇主题不一,但内在的思路则是一贯的:都是力图在复原历史图景、深入既往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。历史当然已经过去,严格来说无从复原,但历史学是永远开放的,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多学科的工具,多参照比对,想想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、另一种理解,由此才能常读常新。这与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类似:它应该是活的,不可抱残守缺,因为事实上,正是新的理论与工具,不断碰撞,才可以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,往前有所推动。
澎湃新闻:我记得您写的“黄道婆之谜”的系列文章,后来甚至改变了历史教科书的叙事,使教科书采纳了您的观点。我很好奇您是否会更为在意学界的评价?或者是说注重跟学界的对话?
维舟:这件事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。起初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一历史叙事中的漏洞,发现上海、海南都在争黄道婆是本地人,但现有的那一点传世史料其实根本不足以证实任何一方的论据;相反,大量的争论其实都是后人的附加想像成分,因为各方往往都夹杂着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。基于我对后现代史学的理解,觉得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剖析个案。完全没想到这篇很快被海南黄道婆学会的诸多学者看到,历史学家郑学檬教授也联系到我,说大体赞同我的观点,并且澳门中学历史课本关于黄道婆事迹的描述,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参照我的意见修改定稿,删去附加成份,因为执笔者是厦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,曾听取郑教授的意见。中学课本里有关黄道婆的文字也会逐次修改,去掉不符合史实的附加成分。
我其实和学界的交流不多,毕竟圈子不同,更主要的是我术业无专攻,写作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,而不是某一类学科(例如经济史),这与现在学界的专业分工不同,也就使我很少会稳定地与某一学术群体密切交流。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个问题,但无奈自己习惯和兴趣如此,一时也无法改变。我当然会注意学界如何回应,毕竟专业意见总要听取,这本身也有助于我自己改进;至于学界评价,对我来说意义也在这里——它可以帮我确认,自己的解释对不对,还有什么改进余地,但这不大会影响我的问题意识,因为我阅读写作的整个动力,是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展开的,这一点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